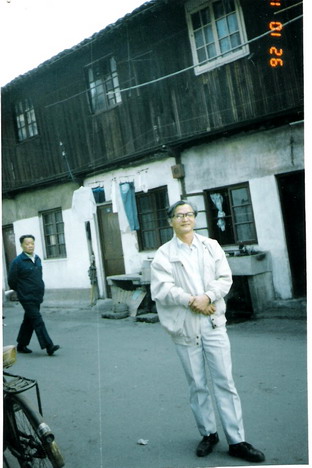1940年(民国二十九年)10月20日(农历九月二十日),我出生于浙江鄞县海曙镇(即今宁波市海曙镇)苍水街102号(后为97号,现已拆除)。苍水街是位于宁波的市中心北面的一条街,宁波人习惯称为“后市”。我出生之前,日寇已经占领上海,侵华日机从上海起飞对宁波地区狂轰滥炸。我的出生地就在苍水街国医街口,距离日寇集中轰炸的市中心不远,险遭炸毁。那时候我家是开水果店的。为了安全和避免惊吓着我,我的父母也不敢打开排门板,让我母亲抱着我躲在柜台底下,上面用被子盖住来消减飞机的轰鸣声。
大约是我出生后第七天(据史料记载是1940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)上午,日机两次入侵宁波上空,低空盘旋。人们奇怪地看到,低空盘旋的日机竟然在开明街一带撒下大量的面粉和麦子等,屋顶上一片淅淅啦啦的声音。当天下午2时20分,日机1架(系日军荣字1644部队所派)飞旋宁波城区东后街与开明街一带上空,又撒下了面粉、麦子、跳蚤等。不久,开明街这一带,莫明其妙地一个接一个地死人,有的是全家都死了。后来人们才知道日本飞机撒的面粉、麦子里的跳蚤都带有鼠疫菌。鼠疫菌已经感染了这里的人,鼠疫已经在开明街一带传布开来。苍水街紧靠着开明街附近的店铺都不敢开门营业,家家户户几乎都紧闭大门。我的父母曾经告诉我说,当时家里要买菜也不许上街,只好在楼上窗口叫住一些胆大的敢于到苍水街叫卖的小贩,从楼上把篮子吊下去买东西。

图为1940年9月5日、10日日机大轰炸后宁波《时事公报》的报道。

图为1940年11月4日《时事公报》的报道。
有一天(据史料记载是1940年11月30日农历十一月初二)晚上,我父亲到开明街的一个混堂(浴室)去洗澡。洗完之后,习惯地在混堂里打瞌睡。由于白天劳累,他睡着了。不久,他被一个外号“瘌痢头”的人猛力推醒。他抬头一看窗外是一片火光,混堂里的人都不知哪里去了。他和“瘌痢头”两人套上衬裤,也顾不上穿上自己的衣服,用混堂的浴巾围住下身就往外跑。到处是火,到处是断墙残壁,两人就迷失了方向,找不到出路。他们在火场里看到有些人被烧死了。为了生存,我父亲和“瘌痢头”就互相帮助,认定一个方向走,终于找到一个被大火烧出缺口的短墙,墙的那一边没有火光。他俩感到这是一条生路,两人就相互帮助,攀上短墙,从火场逃了出来。他们逃出之后,回到家里也不敢和家里人说到这件事,怕家里人害怕。后来听说是当时鄞县政府为防止鼠疫蔓延,有计划将鼠疫隔离区焚毁的,更不敢说了,怕被抓回去。第二天这块地方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场,后来大家都称之为“鼠疫场”。据史料记载,这次焚毁的有民房店铺115户、137间。被烧的店铺都应该是事先通知疏散的,这家混堂怎么会在营业中被烧,就不知原因了。

开明街 “勿忘国耻”碑
据史料记载,1940年10月30日至12月2日,有名有姓染鼠疫死者106人(统一深埋在南门老龙湾〉,其中全家死尽12户、计45人,死人最多一家为宝昌祥西服店,死14人,最早两个死者为滋泉豆浆店主赖福生及其妻子,最后一个死者为居民徐安行。#p#分页标题#e#
历史的哭诉
幸运的是,从鼠疫场逃出的父亲没有感染鼠疫菌,也使当时我这个脆弱的小生命得以逃过这次劫难。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后来,每每说到日本对华侵略或者说到细菌战,父亲总会把这次逃生的经过再说一边,总说自己捡了一条命,要谢谢那位“瘌痢头”。而且说,他在抗战胜利后,还在宁波见到过他,但不知道他后来到哪里去了。据他说,在火场里逃生的恐怕就是他和“瘌痢头”两人,因为他那时还很年轻——28岁,而当时泡混堂的一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。
当时鄞县政府把开明街疫区烧毁,确实是有效控制了鼠疫病菌的蔓延。但是,不可否认的是,也有不少没有感染的老百姓被活活烧死。我的父亲和那位“瘌痢头”,如果不是年轻、不是强烈的求生欲望,也许就会少活38年。
我的命是捡来的。如果当时当局不采取措施,那么鼠疫蔓延的结果,就会失去更多的生命,更没有我这个生命。
那些因感染鼠疫菌而死的人和被活活烧死的人,都是日本对华侵略的罪证!他们的冤魂在地下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!
而今,我还健康地生存着,祈望远离战争,祈望世界和平,祈望永远是和谐社会!我的一位年过八旬的日本朋友也有同感,祈望加强中日间友好交流,愿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相处,愿世界永久和平!